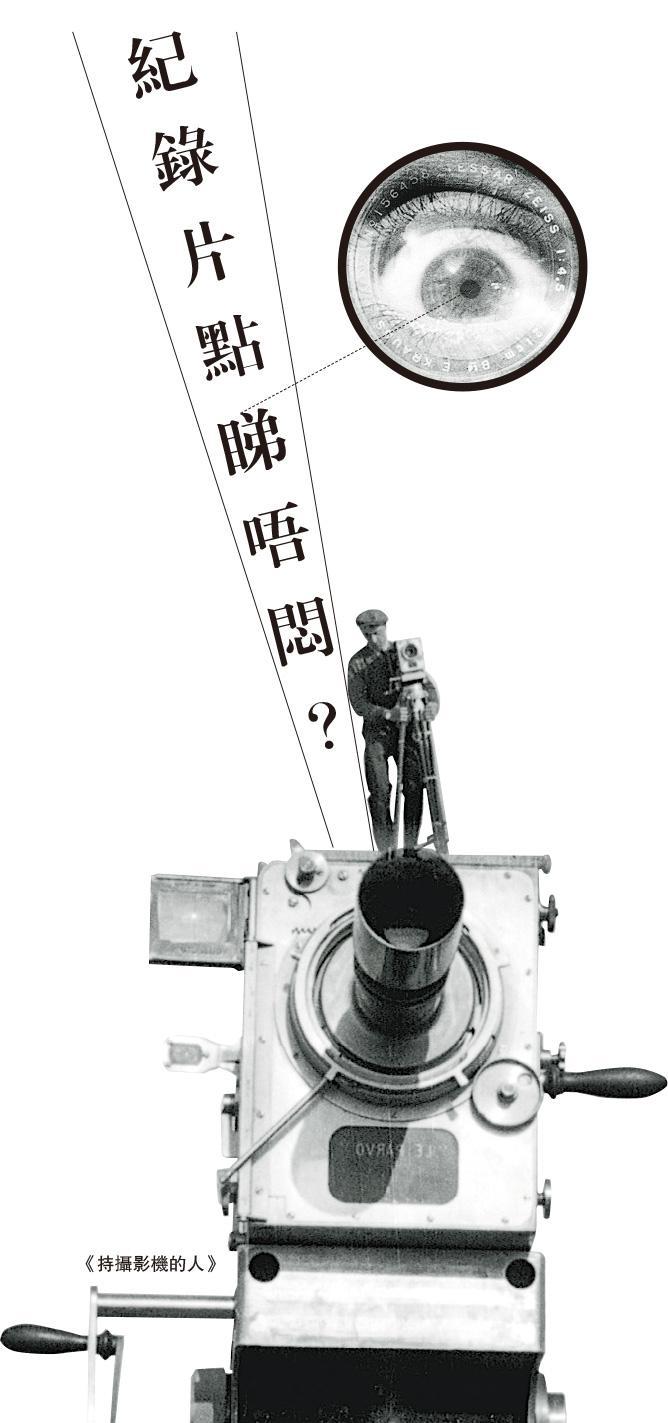【明報專訊】隨着疫情又變嚴峻,不少人回到留守家中的日子,過日辰絕招之一莫過於「睇片」。近年影視發展令我們日常觀影習慣產生變化,有人會瀏覽YouTube去看真實生活點滴和資訊,也有人因Netflix平台上提供更多紀錄片而多了機會接觸這個片種,加上香港經歷兩場社會運動,我們對相關紀錄片更不陌生。時代進化,我們亦是時候擴闊對這些影像的觀影眼光。
電影及紀錄片教育工作者、香港藝術中心電影及錄像部前總監蔡甘銓在課堂上教紀錄片超過10年,他蒐集香港電影資料館的資料作過統計,1970至2000年間在香港戲院公映的本地製作紀錄片有12部(即不計民間電影節及電視等渠道放映作品),不過到了2018 年,該年已有8部,作品雖然多了,然而他有感大眾對此認識不深,與百老匯電影中心開辦一個 18 小時的「雞精」工作坊,惜現因疫情延遲,我們請他介紹將在工作坊講解的幾種模式,先吸收一些精華。電視節目有好多種,其實紀錄片類型都不只以往電視上常見的一兩種,但他強調,不必強行去分一部紀錄片「屬於」什麼模式,很多時作品會兼具幾種元素,當中提及不少經典例子,有些聽落新奇,卻是遠至1920年代的作品,大家可找來看看,擴闊對紀錄片的想像,為認識今天的作品打個底:
Expository Mode(闡釋模式)
政策文宣 與民溝通
蔡甘銓曾在亞視擔任高級編導,解釋「闡釋模式」經常見於電視節目:「如《鏗鏘集》、Inside Story這些公共事務節目,會有出鏡或不出鏡的narrator(敘述者)帶領觀眾看一個議題,做法是以文字為主,如我自己做過《時事追擊》、《時事探索》,運作模式是編輯批准做某個題材後,記者有一兩星期出去做research,然後回來寫稿,寫稿叫story,寫完就拍影像配合文字,我沒辦法說呢個唔好做嗰個唔好做,只是帶人出去拍攝,是以稿為先。」
在1920年代末,被稱為英國紀錄片之父的John Grierson視紀錄片為propaganda(文宣),「現在這個詞附帶很多負面意義,但在20年代則不然,他認為紀錄片有助社會進步,將政府的政策與人民溝通,令他們明白。」若翻出1935年John Grierson的作品 Housing Problems來看看,「開始時有人說明英國爛屋很多,人不夠地方住,便是想推建新樓的政策,就如今日市建局宣傳重建那樣」。
Observational Mode(觀察模式)
拍攝者沒現身 沒旁白解話
不論紀錄片兼具什麼模式,「難免包含觀察模式的拍法」,「闡釋模式有聲帶介入、有『劇本』,而在旁述、記者沒出現時,也會有些『觀察中』的畫面」,發展到極致的程度,是稱為direct cinema的流派,作品鮮有旁述、訪問、配樂。香港導演張虹很多作品採用這種手法拍攝,蔡甘銓列舉兩例,是拍攝2002年慈雲山球場盂蘭節派米活動的《平安米》及兩間band one中學校園生活的《中學》。張虹曾受訪說:「拍攝《中學》時鏡頭不會放在學生的位置去看老師,也不會放在老師的位置去看學生,鏡頭通常是固定地放在一旁,以第三者的角度觀看事情。」「攝影機就是我的眼睛,我看到什麼,觀眾就看到什麼。」
Reflexive Mode(反觀/自省模式)
告訴觀眾有人在拍攝
紀錄片的拍法還有很多好玩的可能,拍攝者可以很隱形,但也有作品故意告訴觀眾有人在拍、有人在剪,讓觀者別太投入,提醒他們縱然事情是真實發生過,也是經過製作團隊選取、處理,才呈現在觀眾眼前。早在1929年的Man with a Movie Camera(《持攝影機的人》)就有大量讓電影製作人「現身」的片段,電影開始時是觀眾魚貫入場的場面,中段又有剪輯一格格菲林的畫面,由此帶觀眾進入不同影像,而片中亦見攝影師身影。
Poetic and Performative Mode(詩學及表演模式)
影像如詩般節奏
Poetic並不只是浪漫詩意,蔡甘銓說「不一定是沙灘兩個人走在一起那種唯美畫面」,他推介必看荷蘭紀錄片導演Joris Ivens的創意,「poetic是一些抽象、具創意的元素,有時這種抽象只是一個節奏」。1929年的Regen(《雨》)較著名,「風吹起漣漪、雨打在窗上、傘重重打開」,以14分鐘畫面捕捉下雨的氣氛,不過別錯過他另一套作品《橋》(De Brug),「完全沒有《雨》那些畫面,是注重節奏」,影片仔細呈現橋開合時部件如何移動,「Ivens及早期的紀錄片工作者受意大利文藝思潮未來主義(futurism)影響,當時的詩會打破一行行工整格式,呈現各種結構,而未來主義也關注machinery(機械),在《橋》裏很長一段是拍那座橋的細件,如一個指標一路向上,另一個指標向下,顯示出機器式的節奏」。
至於表演模式,最明顯可數香港導演陳耀成作品《名字的玫瑰──董啟章地圖》,「一開始有舞者在電車跳舞,來表現他對董文章文字的看法」;另一部1989年的紀錄片Tongues Untied,「則有將黑人處境、受歧視rap出來的部分,裏面亦有舞蹈」。
Participatory Mode(參與模式)
參與當中提問
鄭智雄作品《大禍臨頭》所記的是1995年太子金輪大廈天台屋居民對政府清拆政策的抗爭,其中向政府部門請願一幕,居民與保安發生衝突,然後警察到場拉人,蔡甘銓播放一分多鐘的過程,這些畫面首先是「觀察模式」,「到拍攝者一出聲問警察,就進入了參與模式」。他問警察,「係咪拘捕佢呢請問」、「請問你用咩罪名拘捕佢呀阿sir」、「點解要落手銬呢」,攝影師便已參與其中。
Social Action Mode(社會行動模式)
改變現狀為目的去拍攝
在以上基本可分的幾種模式之外,蔡甘銓另提出「社會行動模式」,他解說一般拍片是拍畢之後交給發行商安排上映、或參加電影節,「作品是主要的」,「但社會行動模式裏,作品不是主要,而是社會行動一部分,是想有轉變才去拍」,觀眾理解這些作品可多留意「電影製作本身及電影後來如何運用」。《華氏911》導演Michael Moore拍過不少諷刺美國社會問題的作品,在《美國黐Gun檔案》(2002)中,Moore將1999年校園槍擊案的受害者帶往Kmart總部,向這間會售賣子彈的連鎖百貨公司追討賠償,公司發言人後來指將逐步安排手槍子彈下架。「整件事是一個社會行動,與鄭智雄的例子同樣是通過參與,作出社會行動。」他認為《大禍臨頭》攝影師質問是在挑戰警察,也是用鏡頭保護示威者。
不過「參與模式」又不必然是社會行動,「看講巴黎人生活的Chronicle of a Summer(《夏日紀事》,1961),電影製作人Jean Rouch和拍檔一開始說這是一個實驗,最後一段戲,二人一路行一路在談,呀我哋呢個實驗成唔成功呢,是參與在作品中,也有自省(reflexive)成分」。
如何以作品促成社會行動,還可看1968年的《熔爐時刻》(The Hour of the Furnaces)。電影片長4個多小時,「當時阿根廷已解放,但拉丁美洲很多地方仍是殖民地。電影第一部分如寫論文般說什麼是新殖民主義,第二部分講阿根廷情况,然後很有創意的是,第二部分完結後打出字幕,說之前看了那麼多,現在會停止放映,進入對話時間,讓觀眾討論自身處境,如香港人就傾香港情况。好可能有人傾到拉丁美洲仍受壓迫,便揸槍出去」,第三部分講民選領袖貝隆上台為何仍招致失敗,如果觀眾在對話時段已經動身行動,就不必再放了。
近年精彩的作品則有《孩子的村子》(2012),中國導演鄒雪平讓村裏的孩子去採訪老人,挖掘大饑荒歷史,「這是來自被稱為中國獨立紀錄片之父吳文光的(民間記憶)計劃,讓一群年輕人到農村拍關於3年大饑荒的紀錄片,當中反駁了官方說法,呈現饑荒是人為災難。鄒雪平先向小孩放以前的片段,讓他們分3組人訪問,以及籌錢為死者立碑。立碑本身就是political action」。
社運與本地紀錄片
「Independence documentary is coming of age」蔡甘銓說。獨立紀錄片製作正趨成熟。香港經歷兩場大型抗爭,我們現在可輕易列舉作品《亂世備忘》、《地厚天高》、《我們有雨靴》,還有許多拍攝2019年的抗爭製作中。他認為獨立紀錄片作品數量增多,要從科技、經濟、社會及政治環境等脈絡,「2000年是分水嶺,那年港台開始將節目製作外判」,涵蓋紀錄片、戲劇。而追溯發展脈絡,自1970年代在香港社會發展富裕,「很多人有能力買Super 8攝錄機」,帶來8米厘的蓬勃發展。另外,繼1967年大學生活電影會成立,「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,許多電影會出現,對於獨立電影的發展也很重要」,來到今天,政治環境亦成為拍攝紀錄片的一大助力。在他看來,以上的經典探索不同模式,香港近期紀錄片則比較單一,「我不是說這些作品不好,如《地厚天高》也是好片」,他認為以上述的各種模式而言,很多近年作品「想抽象一些、要創意的則看不到」,他期待觀眾及紀錄片製作者了解加深後,香港的創作會更多姿多采。
■註
Joris Ivens的經典作品A Tale of the Wind(《風的故事》),以及《孩子的村子》、《熔爐時刻》均會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安排放映,而由蔡甘銓主講的「18小時紀錄片速成班」將會延遲,詳情可留意facebook.com/bc.BroadwayCinematheque資訊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