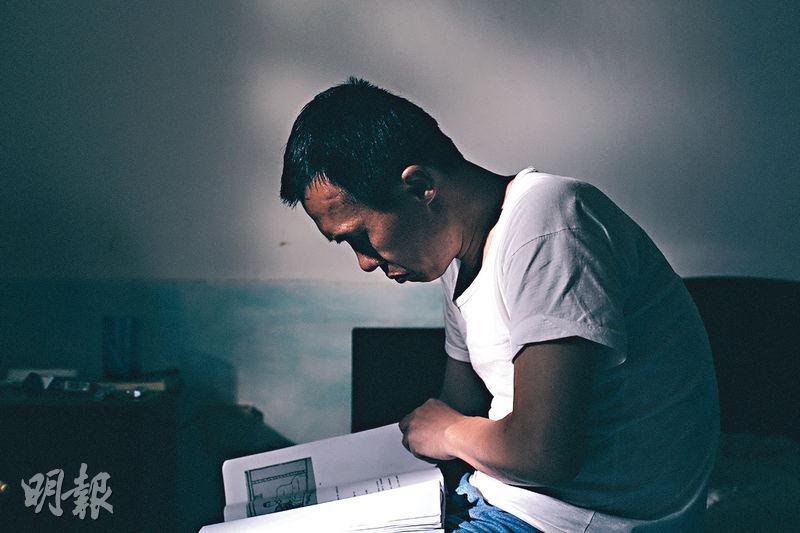【明報專訊】畢贛說,他的電影與詩平行存在,但詩一般更早出現。「詩是在一天的第二十五個小時寫的,但不是每天都有二十五個小時。」他說。所以在詩和電影之間,他更想當導演。訪問裏他常透露自己的惰性,像最近並沒讀詩集,學生時代大多數時間流連在學校的放映室裏,沒系統地看沒人看的電影等。就連開始寫詩,也當是斷句去創作。直到2011年,拍完《老虎》,無法剪接,他以詩作做補釘,才意外發現詩不只是補救,還有互動。
畢贛:「詩是我電影裏面最隱密的一層文本,沒有這層文本,我的電影肯定不完整,但不代表不成立。」在他成長的亞熱帶鄉土裏,他說,詩是鼻子,電影是他的眼睛。
「蕩麥的公路被熄火延長/風經過汽車後備箱/人們在木樓裏行歌坐月/機器伴隨着機器的光/我花了很長時間分辨出痛苦不同於汽油/它可以沉入河流底部/但我希望痛苦能夠揮發/花香無法加重花香潛入水底/記憶卻覆蓋記憶飄在身體表面/人類替代人類掌管家園/地獄顛覆地獄成為天堂」,詩集《路邊野餐》的第一首詩,畢贛用它解釋自己的同名電影,也是戲中主角陳升在如此一個靜謐的夢中的心理狀態。
蹩腳詩人奇幻旅程
2010年,畢贛奶奶的兄長在鎮遠病逝,她買了衣裳想要送給故人,卻因身體問題未能到達鎮遠,於是《路邊野餐》裏,畢贛讓戲中的陳升為老人送上信物,了結心願。從拍攝《老虎》始,他便找姑父陳永忠擔任陳升,在往後的《金剛經》也一樣,畢贛的鏡頭拍的總是陳永忠,一個現實於養療院當保安,臉上總掛着鄉下來的人的尷尬與孤苦,話帶鄉音,四肢時時尷尬得不知如何安置的中年男人——這張寒磣的臉卻活生生是畢贛心中的蹩腳詩人,陳升。
《路邊野餐》裏,陳永忠如常扮演主角陳升,那個無論走到哪裏都能念上幾句新詩,又會開鎖的村醫詩人。他聽人說同父異母的弟弟老歪賣了侄兒衛衛,孩子被一個賣鐘表的男人帶到鎮遠。診所裏老醫生又託他把幾件信物轉交給住在鎮遠的舊情人,於是他離開凱里,前往鎮遠。卻因為沒有火車而停留在叫蕩麥的地方歇腳候船。路上,陳升為遭惡作劇的年輕人解開摩托車的鎖,年輕人駕車載陳升到蕩麥河邊,替他兩臂綁上竹枝,防範野人,最後陳升問他名字,才發現年輕人原來屬於未來;同在蕩麥,陳升認識了年輕人的小情人洋洋,她受託為他補衣服上的鈕扣。陳升於是換上了老醫生打算送給舊情人的花襯衣,並遇上了去世的妻子。他們在貼滿陳年海報的洗髮店裏重逢,他背手彎腰,以贖罪的姿態般讓她梳洗他的頭髮。妻子說她依舊想去看海,於是陳升在理髮店內以電筒照亮了她的拳頭,告訴她掌背透出的紅光就是看到海豚的感覺。
下一個侯孝賢?
「今天的太陽像癱瘓的卡車/沉重的運走整個下午/白醋春夢野柚子/把回憶塞進手掌的血管裏/手電的光透過掌背/彷彿看見跌入雲端的海豚」,《路邊野餐》無題詩之二。
最初,畢贛把電影取名為《惶然錄》,後來監製製片覺得不好。他也覺得《惶然錄》說得太精準,確實不一定好,一時又想不到新名字,便改了另一部正籌備的電影的名字《路邊野餐》,再把後來的新作改名為《地球的最後一個夜晚》。畢贛:「片名不是一個代號編碼,它是一部電影的面孔,是一種禮節。如果你走近我的建築,來到門前,你要敲門,然後等待。」
《路邊野餐》於是像東拼西湊的拼圖,無論在製作還是內容上,電影同在無法想像的緊絀、零碎與隨性中誕生,但成品卻同時達至完整、刻意與嚴謹,因而一舉成名。畢贛只拍了三個月,資金僅二十萬人民幣,戲中大部分演員因成本問題未受專業訓練,如飾演老歪的演員現實中是賣豬飼料的;戲中的小衛衛是畢贛同母異父的弟弟;診所的女老醫生是他奶奶住院時的病友——連畢贛本人也在電影中飾演為人打酒的雜貨店伙計。這部處女電影在他自個兒的挑剔下,依然拿下了法國南特影展的金熱氣球獎、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與盧卡諾影展最佳新導演等多個國際獎項。如此「奇片」也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,外國製片人說戲中長鏡頭將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,多篇影評又指畢贛大有下一個賈樟柯或侯孝賢的模樣,然而內地票房仍然慘淡,作為藝術電影,它把檔期讓路給商業大片,放映場次寥寥,畢贛打趣地說,他的電影只拍給野鬼和風看。直到內地有人在論壇開帖問人《路邊野餐》的評價,他才在帖上隨意留下一首短詩:「用刀尖入水/用顯微鏡看雪/就算反覆如此/還是忍不住問一問/你數過天上的星星嗎/它們和小鳥一樣總在我胸口跳傘」。
和銀河星星相比,再偉大的電影討論起來也顯得渺小。畢贛對評論與讚美看得很輕,並不認為有用顯微鏡去看一套電影的必要。「我能確定的是,我肯定不是大師。拍得好被人誇讚很正常,如果我拍得爛被人唾棄,那也是我活該。所以我並沒有壓力。」畢贛說,他的壓力和不安只會來自寫作中的那些漫長孤單的晚上。
成名這年,他才二十七歲,從小父母離異,他一直與奶奶一同生活,並在名不見經傳的貴州鄉村出生與成長,也就是電影中周圍只得高山,人們無時無刻叼着煙支,打牌取樂,青年人有空便躲進桌球室消磨光陰,醉鬼在白天已經喝得臉紅耳赤的典型老鄉。他身邊的朋友與他一樣,打過不同的工,日子大多過得百無聊賴。寫《路邊野餐》的劇本時,他與錄音師梁凱去拍廉價的婚慶掙錢,開了一間「看花眼婚慶公司」:「我們用很落後的攝影機跟隨着新娘和新郎在酒席中敬酒、穿梭,貴州好像習慣被這種原始的方式記錄相聚與告別。這種影像語言寫實又夢幻,很動人,很接近詩。於是在這部電影裏,我用了一個長達四十分鐘的鏡頭去表現,模糊真實與虛無的邊界,期望觀看的人能體驗一個漫長迷人的過程,企圖獲得一個完整的空間。」電影以宋詞長短句法剪輯而成,那一鏡到底像小時候他看大人們玩牌,出手很慢的那種牌局,當中節奏迷人,他知自己要的就是一樣的感覺。
不存在之地
如此一套帶着個人色彩的公路電影,從凱里走到鎮遠,只有蕩麥這個地方是不存在的。「蕩麥」來自當地的一句苗語,意指隱密的地方。陳升最後並沒有找到老醫生的愛人,也沒有接回衛衛,他坐上年輕人口中不存在的火車,車窗外擦身而過一輛火車,車卡畫上逆時針行走的時鐘圖案,當火車快速前進,圖案交疊,似時間倒流回到過往。畢贛說,蕩麥的存在就像拉美文學經典Pedro Paramo中的科馬拉一樣,是隱藏秘密的地方。
「所有的轉折隱藏在密集的鳥群中/天空與海洋都無法察覺/懷着美夢卻可以看見/摸索顛倒的一瞬間/所有的懷念隱藏在相似的日子裏/心裏的蜘蛛模仿人類張燈結綵/攜帶樂器的遊民也無法傳達/這對望的方式接近古人接近星空」,《路邊野餐》無題詩之八。
這部小說與《路邊野餐》有着相似的目的與藝術手法,主角受快將離世的母親所託,前往名叫科馬拉的地方尋找生父。去到方發現科馬拉是座死城,他在城中四出探問父親的資料,終於從鄉民口中明白父親與科馬拉的前世今生。兩部作品的主角同樣因為失去而開展找尋的旅程,卻在尋找中又印證了失去的必要;同時運用大量時空倒錯,詩一般的節奏,建立時空並存的空間(科馬拉與蕩麥)產生不可能的對話,並於情節內留下大量隱沒的暗示與痕迹,讓人重複去讀仍然找到新的碎屑。
「電影是關於時空的幻覺體驗。我希望用時間長度、建構的空間和角色的動作面孔去表達,就像繪畫裏的線條和顏色。我覺得我要做的就是發掘電影最動人的魅力,讓現實失重。」畢贛說。